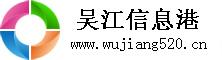纪录片批评沉昱辰:《三里冢之夏》:真实与“穿透力”的探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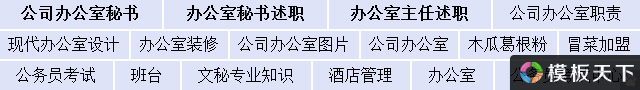
摘 要:小川绅介是日本着名的纪录片导演,有着“日本纪录片大师”的赞誉。《日本解放阵线: 三里塚之夏》是其执导的纪录片《三里冢系列》中的第一部,也是小川绅介所执导的政治纪录片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影片运用纪实的手法,深纳导演纪录的精神内涵,采取一系列实验性探索,使得影像、声响与字幕最大限度的将观众代入到暴力搏斗发生的三里冢现场,震撼人心的同时引起了许多观众深入思考。
《日本解放阵线: 三里塚之夏》是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在“日本新浪潮电影”期间执导的以政治事件为中心、以“农”为题材的纪录片《三里冢系列》中的第一部,也是小川绅介所执导的政治纪录片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世界电影史》一书中曾写道:“日本的纪录影片也有不少杰作。首先应说起的是小川绅介拍摄的一组报道持续多年的阻挠建设成田机场搏斗的纪录片,其现实性达到了迄今为止一般政事纪录片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具有古典军人戏剧的水平。”影片运用纪实的手法,采取了一系列实验性探索,使得影像、声响与字幕最大限度的将观众代入到暴力搏斗发生的三里冢现场,震撼人心的同时引起了许多观众深入思考。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三里冢平民反抗政府权利的行动,得到了日本民主势力、左派人士以及新闻舆论界的支持与同情,小川绅介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不仅从精神道义上对当地农民给予鼓励,而且亲身加入到农民抗征的队伍,成为反对同盟的一员。自从1967年带领领摄制组进驻三里冢开始,历时11年不间断用摄影机记录下农民守土抗暴的真相,通过记述三里冢农民反对机场强制建设的抗争,书写下一部饱含真情的暴力斗争史诗。
《三里冢之夏》的诠释离不开小川绅介所具有的记录精神。首先是他对时间的执着,一直将时间作为拍摄纪录片的重要因素考虑,影片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得以呈现离不开其对时间的把控。摄制组长期坚守在拍摄现场的前线,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下对同一个主题进行拍摄追踪,细致入微地还原事情的真相,使得影片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真实表达”。而在真实方面,小川绅介要求对真人真事不加修饰的拍摄记录,几乎舍弃蒙太奇的运镜模式,只为了保留最本来的真实。除此之外,他在创作中对“土地与农民”主题的热诚,贯彻了三里冢系列全部作品。小川绅介是从始至终斗争着的,不论是拒绝旁观的影像拍摄还是将纪录片作为武器鲜明地表达自我的观点,“都有着对土地与农民绝对不能放弃的立场,而任何关于其立场的苛责似乎都会在这份精神的映照下自行暗淡。”
若抛开小川绅介纪录片中的介入社会斗争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转而挖掘影片记录与表达的方式时,不难发现,《三里冢之夏》是小川绅介不断尝试的实验性探索,也是他第一部探索对暴力进行电影化的实验影片。纵览纪录片发展历史,从诞生之日起便一直与实验电影、先锋电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约翰·格里尔逊曾有观点:“没有实验,纪录片就失掉了它的价值;没有实验,纪录片便不存在”。与其他记录三里冢这场农民权利斗争的纪录片一样,《三里冢之夏》令人印象深刻,发人深省。影片中的画面相当极端,利用晃动的手持摄影,摄影机的凝视,连续画面间的叙述停滞,对动、静态场景的交叉编排以及银幕内外的纪录影像等摄录方法,探索着暴力向的电影化表达,赋予了纪录片内在的影响力。而这一探索不仅仅是对屏幕影像的实验,更是对屏幕外时空的延伸。
在《三里冢之夏》中,小川绅介将晃动的镜头作为主要方式,记录下三里冢发生斗争的场景。同其以往的电影一般,影片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手法呈现出警察与农民发生骚乱的暴力现场。“我之所以尽量想同步拍摄,是因为在现实中我看到的是具体而带着色彩的正在说话的人。所以不能容忍对画面进行切割的拍摄方法。可能的话,我恨不得把面前的人,直接塞到摄影机里去。”在追求影片最大限度还原现场的真实性理念下,“摄影师会在战斗爆发时加入防暴警察与农民的斗争空间,穿梭在现场的冲突与混乱之中。”用摄像机拍摄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记录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贯性,直接向观众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场景的混乱和人物之间的差异在纪录片中暴露无遗,有效地加强了影片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影片中的冲突是愤怒而混乱的,农民与防暴警察产生连续的肢体冲突动作,双方斗争中反复争执推搡的场面都被摄影机记录下。观众通过不断移动的摄影机镜头持续跟踪被摄主体,并随着摄影机的运动直观地了解到这一时间段内三里冢地区遭遇的破坏,以及人民群众遭受到身着制服的防暴警察所代表的象征着政府当权者的攻击。这种猖獗的动作场面很容易被抖动的手持摄影所加重和渲染。虽然与电影采访和讨论中使用的固定镜头不同,甚至从视觉角度来看完全相反,但剪辑很大程度上已经在这些长镜头中完成,这种镜头空间的模糊观感和快速跳跃的画面衔接给人一种剪辑迅速的感觉。
影片中,成田的一个农妇和她的女儿为苦守故土,在防暴警察来临之前,相互用铁链将自己绑缚在树干上,她们为了防止警察投放烟雾弹都戴着口罩,两个人的身上都挂着一张牌子,上面写着:“一棵树就是一个孩子,一棵树就是一个女人”。天色阴沉,下着大雨,两个人四周不断有防暴警察往返踱步,但母女两人都面色平静,对入侵家园的人毫无恐惧。另一组画面里,一个瘦削的农妇面对一排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警察说:“你们回去吧。你们知道吗,这里是我们住了好多年的地方,我们不能离开。你们能明白吗?”农妇循环往复地说着这些话,警察们却没有人应答。有孩子爬上树梢,大声高喊:“绝对不能让政府的军队砍到大树!”
纪录片带着全部真实的力量不停地冲击着观众,拍摄者站在农民的目标与立场上,通过坚定地站在被压迫农民的一方,冲到暴力实施的第一线,用并非隐藏的摄影机真实地记录下一切,毫不留情地进行控诉与指责,从“血肉与铁链、热诚和冷酷、话语与缄默、乞求同无奈的对峙”中,让观众自行领悟镜头内涵与摄影者意图,并理性地作出判断。不难看出,影片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阻止日本政府占用农民土地建设新机场。观众可以从纪录片中的一些场景看出摄制组极强的指向性。比如日本政府雇佣的的“机动队”以两万日元的日薪上岗,而对面的农民只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之抗衡。透过农民之间的真实对抗,深刻体现了农民对土地的怀念,让观众感受到一种超越民主的情感,一种关于如何真正“活下去”的情感。
在拍摄理念上,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与小川绅介具有某些方面的相同,该理论将摄影机比作人的眼睛,主张不主观介入电影的拍摄,而强调一种拍摄的旁观性。“观察模式需要借助电影制作者的看似缺席或是他对于所记录事件的不加干涉来表达。”观察模式中,角色们往往会陷入一些自身的迫切需求或危机,这类事件将占据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忽略影片创作者的存在。观众根据有意无意观察到的行为进行推理再得出结论,而电影的创作者退到了一个观察者的位置,观众在决定电影所展示的内容的意义上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小川绅介在保留了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以及相关运用的基础上,发掘出自己独具一格的创作理念。
在影片中,小川绅介摄制组习惯使用较为固定的长镜头来解释事件的背景和发展历程,在确保纪实内容的真实性的同时完整地还原现实的情况气氛。在《三里冢之夏》的一处场景中,影片的画面定格在摄影师田村正毅拍摄途中被警察殴打拖拽的一幕上,然后变成了全帧字幕“B机位开启”。此时,面对暴力的施行者,摄影机充分地发挥了其凝视的作用:随着镜头换向远处,观众的注意力伴随着摄影机缓慢拉进,银幕上随即呈现出许多防暴警察的头部,紧接着是面部表情。令观众直面警察,而不是仅仅通过他们外在的肃穆制服形象认识他们,这显得纪录片更加具有揭示性的意义,在小川绅介影片中是第一次。
除此之外,特写的拍摄选择了走入到斗争中实施暴力的人民中,悄无声息地把镜头对准了他们的脸部,清晰地记录下了每一个无法遮掩的神情,而非将镜头放置在较为安全的位置用长焦镜头对防暴警察进行拍摄。因此,在宛若眼前的距离内,警察们手中的武器装备无法发挥作用对他们进行防卫,也无法进行以暴制暴,只能任凭镜头的眼睛审视和斥责他们的身心。透过影片的镜头,能够看出警察在“面临审视”时眼神闪躲,不断逃避着灵魂与良心上的责难。然而镜头对此毫不留情,捕捉他们逃避的目光并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这里,镜头随着观众的目光向外延伸。
而这很好地展现出摄影机镜头所具有的“凝视”力量,在这个最重要的场景中,小川绅介表现出了内置于镜头轴线中的穿透力。本文根据叙事电影理论,从实验电影的角度探讨了小川绅介相机的“凝视”功能。这一聚焦通常被认为是个体差异的人的状态,与传统的叙事电影理论中叙述的投射观众欲望的凝视有所区别。取而代之的是对施暴者的审视,展现了纪录片中“凝视”的力量,也包含了非虚构电影中的穿透力,看透内里,是对“以摄影机为武器”的有力诠释。
《三里冢之夏》的实验性探索主要体现在连续的暴力场景转换间短暂停滞的间隙,伴随着有节奏和律动的运动和静态的交织,看似平静的静态场景中往往都酝酿着即将爆发的剧烈骚动。不断交替变换的静态场面与动态的斗争抗议场景,就像是乐谱上有转折性的节奏变化。根据詹姆斯·托拜厄斯对于纪录片音乐性的观点,马克·诺恩斯曾经提出认为小川绅介拍摄的影片蕴含有极好的音乐性。“托拜厄斯的着作为思考电影与音乐性开拓了新的领域,他认为音乐性是一种表述话语,将主体与客体像集体一般联结在一起,同时反对将音乐与影响划分为有情感与意义的二元结构。”
这样动静结合的韵律感同样体现在影片的空间上,在拍摄正在发生着暴乱的场景中,小川绅介偶尔会把对立的双方放在一边,在影片的一些暴力情形中,不仅将注意力集中在骚动的细节上,将暴力的主要实施者被放在一边,将镜头瞄准场景中的细节和空间中次要人物不受控制的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持续的暴力搏斗和抗衡节拍,但这些和平时刻只是为了将影片推向最后的峰值,当画面中不时闪过双方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夹杂着施暴者歇斯底里的叫喊,足以让银幕前的观众感受到当时三里冢扑面而来的炽烈情感。
《三里冢之夏》发生的一场激烈对抗中,部队慢慢逼近人群与村庄,兵士们将树林围得密不透风,在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上,农民和防暴警察两方紧张地对峙着,气氛中对暴力的酝酿已然接近临界点,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令人屏住呼吸的局面被一群骑车上学的孩子打破了,恶战一触即发。与此同时,摄影机缓缓地向向一棵参天大树的树梢拉去,只见在大树的顶端有一个孩子双手紧紧地环抱着树杈,看不清脸,只觉得是极悲惨的。场面短暂安静了几秒后,便出现有好几个警察,猛地从四周向前冲去,围绕着孩子所在的大树大力地摇曳起来,近乎疯狂。镜头一转,孩子背靠着苍凉的天空身体不停地晃动着,眼见摇摇欲坠,生命危在旦夕。紧接着一个母亲奋不顾身地冲向那群身强力壮的军人,她嘶吼得肝肠寸断:“救救孩子!脱下你们的制服,救救孩子,救救我们的森林!”
内地女导演彭小莲曾在回忆小川绅介的书中描述自己观看这段影片后的感受:“这是纪录片啊,这是一个实实在在被记录在胶片上的生命。我们和银幕上的母亲都开始嘶喊起来,你不会再记得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你知道这是生命!她们用生命在嘶喊,摄影机几乎是贴着人脸在拍摄,你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人,包括摄影师都处在危险之中,所有的人都将生命献给了这片土地和森林。”
除此之外,作为一部实验性纪录片,小川绅介对在暴力冲突中失控的次要人物个性的关心,为纪录片的叙述节奏增添了独特的体验。镜头关注着斗争现场微妙和看似次要的细节,例如一名在斗争中失控的机场建筑员工,为了清理出汽车通过的道路,他猛烈地攻击身边拥挤的农民,此时他处于斗争双方的中间。然而很快他的声音便重新淹没在现场的喧嚣中,重新将画面的主战场交回了对立双方。
基于此,《三里冢之夏》不仅没有陷入道德主义的政治评论,反而是进一步考察了事件的直接性,仿佛这些事件就发生在现场,观众就是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而影片中处于这场斗争边缘看似无足轻重的人物和行为,都会通过变换的镜头,逐渐靠近舞台的中心,共同形成影片的最终表达。
《三里冢之夏》作为纪录三里冢农民权利抗争的“暴力史诗”的开篇之作,真实生动地还原了现场,令人深刻感受到导演小川绅介的纪录精神。对时间要素的坚守,力求纪录片影像客观与真实的表达,心系农民与土地,对生活的理解以及以纪录为武器的独立意识,使得影片饱含纪录精神。同时,影片做了许多实验性手段的探索与运用,在相当多篇幅中采用极端晃动的手持摄影,穿插着出现在传统纪录电影中少有的“凝视”镜头,展现出不同于叙事电影理论影片的精彩表达,赋予了纪录影片非凡的能量与穿透心灵的震撼力及审视度。同时,通过富有律动感的动静结合与交迭,加深了对暴力现场的刻画,在最大限度内将观众代入真实事发现场,亲临当年暗流涌动的斗争场面,指引着观众沉思,将价值、精神与摄影者的拳拳之心毫无保留地托举至我们面前。
[1][美]比尔·尼科尔斯着,陈犀禾、刘宇清译,纪录片导论(第二版)[M].2016:195
[2]彭小莲. 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裴鑫.暴力的电影化实验——《三里冢之夏》的暴力书写[J].剧影月报,2021(05):34-36.
[4]王迟.纪录片与实验电影的关系:对聂欣如教授的回应之三,南方电视学刊[J].2015(01):66-70.
[7]周雪峤.不再“旁观”——从小川绅介到原一男的日本述行纪录片[J].中国电视,2019(05):94-99.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必修课《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2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2年优秀影视评论”)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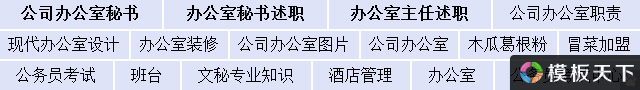

相关文章:
- [美食资讯]烂(làn)租(zū)网友是怎么说
- [美食资讯]“干对岸拍的比观光局还好”!
- [美食资讯]16亿人正在B站看纪录片《人生
- [美食资讯]推荐10部大快人心的复仇片以暴
- [美食资讯]男子喜当爹第三天发现儿子非亲
- [美食资讯]老人带孙天经地义?其实索要“
- [美食资讯]天九共享在阿布扎比获评“最具
- [美食资讯]命由己定无怨无悔
- [美食资讯]十堰天气预报15天
- [美食资讯]天能股份(688819)_股票行情_走
- [美食资讯]又关注补齐民生短板
- [美食资讯]伴随奖项影响力的提升
- [美食资讯]讲述沉争一宋祖儿饰邵北笙王安
- [美食资讯]通过规则制度支持策略
- [美食资讯]推动企业从投入到产出的全产业
- [美食资讯]蔷薇资本成立于2017年
- [美食资讯]超过150万户小农户从中受益
- [美食资讯]再到我和我的祖国你好
- [美食资讯]助眠产品使用程度较低
- [美食资讯]这便是人和自然相互成就的最好

- 最后你的样子究竟是什么原因?
- 有关宠(chǒnɡ)鳞(lín)这到底是个什么梗?
- 淮南手链姐有没有后续报道?
- 炫舞暴走的鼓手又是个什么梗?
- 比亚迪裁员后续报道是什么?
- Eason陈奕迅完成诸多挑战
- 生化末日之重活暴君这是个什么梗?
- 有关空之境界第一章俯瞰风景这是不是真相?
- 关于窟施(shī)狗(ɡǒu)骏(jùn)雇(ɡù)到底是怎么
- 幸福储备魏斯婷究竟怎样?
- 有关相(xiāng)亲(qīn)相(xiāng)爱(ài)这又是个什
- 腋窝淋巴结检查顺序究竟怎么回事?
- 有关小时代票房网友会有什么评论?
- 富家子开保时捷碰瓷:专挑酒驾豪车一年作案20余起涉案
- 有关失落大陆多木木多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 关于与青春有关日子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 意大利灯具这是不是真相?
- 关于表演女班男助教什么情况?
- 武财神爷摆放位置真相是什么?
- 关于杨贵妃向海岚看看网友是如何评论的!
- 关于重生之王语嫣最新消息!
- 关于豫东红脸王陈建设又是什么梗?
- 福迪雄狮皮卡是真的吗?
- 关于超级跑跑名字是怎么回事?
- 汤姆逊烈龙什么原因?
- 他在那里站岗是怎么回事?
- 关于为什么没有天与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 椒(jiāo)渴(kě)惦(diàn)土(tǔ)有没有后续报道?
- 律跪抵葱网友会有什么评论?
- 有关苏西河南有没有店面这是不是真相?
- 一千个冷笑话到底是个什么梗?
- 奥沙利文塞尔比网友是如何评论的!
- 阳西沙扒湾究竟什么情况?
- 一无所得(yī wú suǒ dé)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 心灰意冷(xīn huī yì lěng)又是个什么梗?
- 颠倒乾坤影评具体内容是什么?
- 爱丽舍说明书到底是什么情况?
- 关于门当户对(mén dāng hù duì)这件事可以这样理
- 奔驰大G有多少个G?分分钟让你明白大G有多不好惹
- ronjeremy后续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