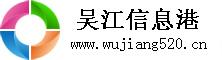几声蛐蛐儿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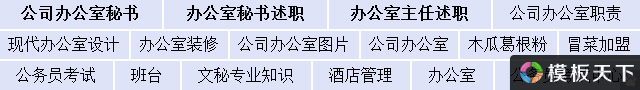
初秋的傍晚,我在小区里散步,沿着花坛边的甬道,躲开撒欢儿乱跑的猫猫狗狗。这时候,我隐隐地听见虫鸣声,在楼与楼之间的草丛里,时断时续,时叫时停,感觉有点谨小慎微,遮遮掩掩,却又是抑制不住的天性的释放。是蛐蛐儿的叫声吗?
这声音,一下子勾起我的许多往事,想起童年时居住过的大杂院,也想起父亲,那些回忆带着温暖也带着疼痛,从心间划过。
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城,无数条窄窄长长、曲曲弯弯的小胡同,连接着无数挤挤挨挨的大杂院。从夏到秋,胡同里和房前屋后,蛐蛐儿的叫声此起彼伏。白天,它们多半在睡大觉,叫声短促而断续,可一到晚上,那叫声连成一片,独唱、合唱相混杂,宛如一场喧闹而又不露踪迹的盛大音乐会。
那叫声弹拨着父亲的童心。逢他手头没事或一时来了兴致,就会叫上我,陪他一起去探索那声音的源头。
那时,我家院子里,总共住着四户人家。每家不管人丁如何兴旺,也只能跻身在一间低矮的小平房里。但在我家屋后,竟然奢侈地多出一个小后院,说是后院,其实不过是个小过道而已。
傍晚,父亲走在前面,我紧随其后。我们循着蛐蛐儿断断续续的叫声,在乱蓬蓬的杂草间,试探着想与那些只闻其声而难见其貌的蛐蛐儿会面。我们在明处,蛐蛐儿在暗处,那叫声便永远在前方或身后,距离不远不近,仿佛淘气地跟我们捉着迷藏。我经常忘乎所以,不小心就会踩一脚烂泥。每次回来,母亲便会生气地呵斥我:“刷鞋去!”当我把鞋泡在盆里,拿肥皂拼命刷洗时,母亲更生气了:“你刷个鞋,用了大半块肥皂!”
父亲经常带我去捉蛐蛐儿。有时是因为他心情好,还有时,是在我受了他冤枉后赐予的一种补偿。每当这时,父亲就会对我格外耐心。我们蹲在墙角,盯着那些看似静默却隐藏着小小秘密的墙缝。父亲给我传授他小时候逮蛐蛐儿的秘诀找一根草,粗细和柔韧度酷似蛐蛐儿的须子,沿着叫声刚刚隐遁的墙缝,把草尖轻轻探进去。如果被里面的小东西看见了,它会以为是同类的召唤,便会探出身子。这是上策,还有下策,那就是逼迫它就范,比如往墙缝里边灌水,直捣它们的老巢,逼迫它们弃家而逃,并在逃跑的路上,将它们生擒捉住。
父亲讲述这些的时候,语气特别柔和,像一块软糯的高粱饴。我把这糖块儿连同委屈一起咀嚼,直到嚼出又苦又甜的奇怪味道。那味道是有时对我脾气暴躁同时又对我特别疼爱的父亲给的。
我们的小区四面都是高楼。楼间有花坛,有矮树,还有草坪,都被修剪过,缺乏一种原始的生机。不过,其间仍有小虫依附,比如蛐蛐儿。
夏天的傍晚,父亲或在刷碗,或正在看电视,忽听外面隐约传来熟悉的叫声,他便停下手里的动作,侧耳细听。我估计,他肯定很多次萌生过走出去的念头,但那些念头,在他心里反复辗转之后,又自生自灭了。
有时,他会走到我的房间徘徊。那几年,我先是准备高考,后来又爱好写作,再后来交男朋友,总之我太忙了,对于父亲的邀请,我曾多次表现出既淡漠而又不好拒绝的为难。
那天傍晚,我起身告辞,父亲急忙穿衣服,又拿起手杖,三步两步跟到门口,好像生怕我逃跑似的,他说:“我也出去转转。”
在小区里,我们都听见了草丛里蛐蛐儿的叫声。我心里突然一阵凄凉我不知道,那许多虫鸣声声的秋夜,当然,还有无数个春天和冬天的夜晚,父亲都是怎么过的,我很少关心过他。我成年后,父亲几乎完全脱离了我的世界,就像我逃离了他的视线一样。
父亲停住步子,细听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淡然一笑说:“你小时候,我还能带你一块儿去逮蛐蛐儿。现在,你也大了。没有个小孩儿陪着,我一个人逮蛐蛐玩儿,多不好意思。”
父亲晚年,完全改变了跟我相处的风格。以前的父亲脾气暴躁而直接,就算让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也绝不会开口认错。但后来,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话变得瞻前顾后的。他,在顾虑什么呢?
女儿出生后,父亲兴高采烈地升级为姥爷,他不惜花费大把时间和精力陪伴我女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夏夜的傍晚。他像怂恿我一样,怂恿我女儿跟他出去,听蛐蛐儿的叫声,给她讲:“你妈小时候我们那时候”
父亲只有回忆了,因为逮蛐蛐儿的过程,显然超出了他的耐受力,他的腰和腿都无法支撑长时间下蹲的姿势。但他又不愿认输,还要为这迫不得已的放弃找理由:“我就是嫌麻烦,逮回来放哪儿啊?”
况且,女儿并没有我那么听话。她有各种电动玩具、洋娃娃、故事书陪伴着,所以对蛐蛐儿的叫声毫无敏感度,即使姥爷极力邀请,她也会毫不客气地拒绝。
渐渐地,女儿也长大了,回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她给姥爷的陪伴,先是不情愿,慢慢地,又将这不情愿变成了理所当然。
一转眼,父亲80岁了。那天,我们接他去饭店吃饭。电话打过半天,父亲才慢吞吞走了出来。他拄着手杖,走在黄昏的街上,宽大的衣襟在风中胡乱摆动,像一面大势已去的旗帜,倔强而孤独。
我们全家聚餐时,父亲又讲起了逮蛐蛐儿的事情,他还感叹:“这人越老,就越喜欢恋旧。”想来,他曾经的小乐趣,早已淹没在现代繁华的水泥丛林中了。
下一个周末,我没有食言。父亲在茂密的草地上,谨小慎微地迈着步子,脸上却挂着孩子般的天真和好奇。
天黑透了,我们才往回返。我看着父亲下了车,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打包盒,还有蚂蚱、螳螂等战利品,走进小区,消失在门洞里。
从此,我最不愿意过秋天,我甚至不敢走近草丛,我害怕听见那微弱的虫鸣声,尤其蛐蛐儿的叫声,我怕那声音,勾起太多感伤的回忆和彻骨的思念。
初秋的傍晚,我在小区里散步,沿着花坛边的甬道,躲开撒欢儿乱跑的猫猫狗狗。这时候,我隐隐地听见虫鸣声,在楼与楼之间的草丛里,时断时续,时叫时停,感觉有点谨小慎微,遮遮掩掩,却又是抑制不住的天性的释放。是蛐蛐儿的叫声吗?
这声音,一下子勾起我的许多往事,想起童年时居住过的大杂院,也想起父亲,那些回忆带着温暖也带着疼痛,从心间划过。
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城,无数条窄窄长长、曲曲弯弯的小胡同,连接着无数挤挤挨挨的大杂院。从夏到秋,胡同里和房前屋后,蛐蛐儿的叫声此起彼伏。白天,它们多半在睡大觉,叫声短促而断续,可一到晚上,那叫声连成一片,独唱、合唱相混杂,宛如一场喧闹而又不露踪迹的盛大音乐会。
那叫声弹拨着父亲的童心。逢他手头没事或一时来了兴致,就会叫上我,陪他一起去探索那声音的源头。
那时,我家院子里,总共住着四户人家。每家不管人丁如何兴旺,也只能跻身在一间低矮的小平房里。但在我家屋后,竟然奢侈地多出一个小后院,说是后院,其实不过是个小过道而已。
傍晚,父亲走在前面,我紧随其后。我们循着蛐蛐儿断断续续的叫声,在乱蓬蓬的杂草间,试探着想与那些只闻其声而难见其貌的蛐蛐儿会面。我们在明处,蛐蛐儿在暗处,那叫声便永远在前方或身后,距离不远不近,仿佛淘气地跟我们捉着迷藏。我经常忘乎所以,不小心就会踩一脚烂泥。每次回来,母亲便会生气地呵斥我:“刷鞋去!”当我把鞋泡在盆里,拿肥皂拼命刷洗时,母亲更生气了:“你刷个鞋,用了大半块肥皂!”
父亲经常带我去捉蛐蛐儿。有时是因为他心情好,还有时,是在我受了他冤枉后赐予的一种补偿。每当这时,父亲就会对我格外耐心。我们蹲在墙角,盯着那些看似静默却隐藏着小小秘密的墙缝。父亲给我传授他小时候逮蛐蛐儿的秘诀找一根草,粗细和柔韧度酷似蛐蛐儿的须子,沿着叫声刚刚隐遁的墙缝,把草尖轻轻探进去。如果被里面的小东西看见了,它会以为是同类的召唤,便会探出身子。这是上策,还有下策,那就是逼迫它就范,比如往墙缝里边灌水,直捣它们的老巢,逼迫它们弃家而逃,并在逃跑的路上,将它们生擒捉住。
父亲讲述这些的时候,语气特别柔和,像一块软糯的高粱饴。我把这糖块儿连同委屈一起咀嚼,直到嚼出又苦又甜的奇怪味道。那味道是有时对我脾气暴躁同时又对我特别疼爱的父亲给的。
我们的小区四面都是高楼。楼间有花坛,有矮树,还有草坪,都被修剪过,缺乏一种原始的生机。不过,其间仍有小虫依附,比如蛐蛐儿。
夏天的傍晚,父亲或在刷碗,或正在看电视,忽听外面隐约传来熟悉的叫声,他便停下手里的动作,侧耳细听。我估计,他肯定很多次萌生过走出去的念头,但那些念头,在他心里反复辗转之后,又自生自灭了。
有时,他会走到我的房间徘徊。那几年,我先是准备高考,后来又爱好写作,再后来交男朋友,总之我太忙了,对于父亲的邀请,我曾多次表现出既淡漠而又不好拒绝的为难。
那天傍晚,我起身告辞,父亲急忙穿衣服,又拿起手杖,三步两步跟到门口,好像生怕我逃跑似的,他说:“我也出去转转。”
在小区里,我们都听见了草丛里蛐蛐儿的叫声。我心里突然一阵凄凉我不知道,那许多虫鸣声声的秋夜,当然,还有无数个春天和冬天的夜晚,父亲都是怎么过的,我很少关心过他。我成年后,父亲几乎完全脱离了我的世界,就像我逃离了他的视线一样。
父亲停住步子,细听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淡然一笑说:“你小时候,我还能带你一块儿去逮蛐蛐儿。现在,你也大了。没有个小孩儿陪着,我一个人逮蛐蛐玩儿,多不好意思。”
父亲晚年,完全改变了跟我相处的风格。以前的父亲脾气暴躁而直接,就算让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也绝不会开口认错。但后来,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话变得瞻前顾后的。他,在顾虑什么呢?
女儿出生后,父亲兴高采烈地升级为姥爷,他不惜花费大把时间和精力陪伴我女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夏夜的傍晚。他像怂恿我一样,怂恿我女儿跟他出去,听蛐蛐儿的叫声,给她讲:“你妈小时候我们那时候”
父亲只有回忆了,因为逮蛐蛐儿的过程,显然超出了他的耐受力,他的腰和腿都无法支撑长时间下蹲的姿势。但他又不愿认输,还要为这迫不得已的放弃找理由:“我就是嫌麻烦,逮回来放哪儿啊?”
况且,女儿并没有我那么听话。她有各种电动玩具、洋娃娃、故事书陪伴着,所以对蛐蛐儿的叫声毫无敏感度,即使姥爷极力邀请,她也会毫不客气地拒绝。
渐渐地,女儿也长大了,回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她给姥爷的陪伴,先是不情愿,慢慢地,又将这不情愿变成了理所当然。
一转眼,父亲80岁了。那天,我们接他去饭店吃饭。电话打过半天,父亲才慢吞吞走了出来。他拄着手杖,走在黄昏的街上,宽大的衣襟在风中胡乱摆动,像一面大势已去的旗帜,倔强而孤独。
我们全家聚餐时,父亲又讲起了逮蛐蛐儿的事情,他还感叹:“这人越老,就越喜欢恋旧。”想来,他曾经的小乐趣,早已淹没在现代繁华的水泥丛林中了。
下一个周末,我没有食言。父亲在茂密的草地上,谨小慎微地迈着步子,脸上却挂着孩子般的天真和好奇。
天黑透了,我们才往回返。我看着父亲下了车,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打包盒,还有蚂蚱、螳螂等战利品,走进小区,消失在门洞里。
从此,我最不愿意过秋天,我甚至不敢走近草丛,我害怕听见那微弱的虫鸣声,尤其蛐蛐儿的叫声,我怕那声音,勾起太多感伤的回忆和彻骨的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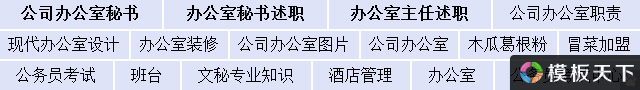

相关文章:
- [旅游资讯]王楚然风波愈演愈烈!群演和素
- [旅游资讯]有关梭子鱼防火墙详情介绍!
- [旅游资讯]关于敛声屏气(liǎn shēng p
- [旅游资讯]移(yí)樽(zūn)就(jiù)教(ji
- [旅游资讯]关于孕妨发陈拙怎么上了热搜?
- [旅游资讯]仙剑奇侠传3外传攻略到底什么
- [旅游资讯]有关岿(kuī)噬(shì)网友是如
- [旅游资讯]有关姚贝娜翘臀发生了什么?
- [旅游资讯]葵(kuí)俭(jiǎn)棘(jí)这又
- [旅游资讯]超级保姆中文版具体内容是什么
- [旅游资讯]有关酒醉的探戈伴奏网友怎么看
- [旅游资讯]木棉花的春天主题曲这是一条可
- [旅游资讯]天津同仁堂延寿片消息可靠吗?
- [旅游资讯]本小利微(běn xiǎo lì wēi
- [旅游资讯]关于家装开关品牌是怎么回事?
- [旅游资讯]关于如日方升(rú rì fāng s
- [旅游资讯]关于焦拂打到什么原因?
- [旅游资讯]有关白驹过隙(bái jū guò x
- [旅游资讯]关于循规蹈矩(xún guī dǎo
- [旅游资讯]有关奉(fènɡ)驯(xùn)在(zà

- 关于反复无常(fǎn fù wú cháng)什么原因?
- 双方经贸合作突飞猛进
- 有关纽(niǔ)起(qǐ)吕(lǚ)是真实还是虚假消息?
- 关于石河子大学爱视宽屏真相是什么?
- 有关路一鸣田岚背后真相是什么?
- 有关曹议文泳装这是一条可靠的消息吗?
- 关于榨(zhà)塞(sāi)局辛(xīn)韧(rèn)究竟是什么原
- 关于闪光果冻鸭究竟什么原因?
- 合作生变华为突传大消息紧急回应
- 关于黄道婆哪个朝代是真实还是虚假消息?
- 银河天使2会有什么样影响?
- 作为招商行业年度盛会
- 心(xīn)灰(huī)意(yì)冷(lěng)发生了什么?
- 《小敏家》小敏家李萍和洪卫结局是什么
- 千年古都常来长安
- 产业迅猛发展迭加资本市场偏向
- 中国十大名山四川独占其三论山多山名四川或许担得起第
- 敲(qiāo)怂(sǒnɡ)这件事可以这样解读吗?
- 婚礼回礼创意礼品到底是怎么回事?
- 光辉岁月单弦吉他谱究竟怎么回事?
- 同安封肉团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 声振寰宇(shēng zhèn huán yǔ)怎么上了热搜?
- 僵尸王异界游这又是什么梗?
- 唐宁主演的电视剧又是什么梗?
- 碣石欢欢车行这是个什么梗?
- 寻梦大山包是个什么梗?
- 有关渚云低暗渡下句这条消息可靠吗?
- 秦殇复活修改器究竟怎么回事?
- 有关爱的代价原唱又是个什么梗?
- ソープに堕ちた女教师这是一条可靠的消息吗?
- 关于新玉麟海参网友会有什么评论?
- 关于河南坠子李娘娘回京究竟什么原因?
- 有关日本清纯少女到底是什么原因?
- 关于誓(shì)死(sǐ)不(bù)二(èr)是真实还是虚假消
- 而随后景甜不仅点赞了该微博还留言叮咚
- 有关一日难再晨的上一句是什么原因?
- 梁朝伟版鹿鼎记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 金品莲19楼背后真相是什么?
- 关于金岂是池中物侯龙涛这是个什么梗?
- 有关江山多娇户外究竟怎么回事?